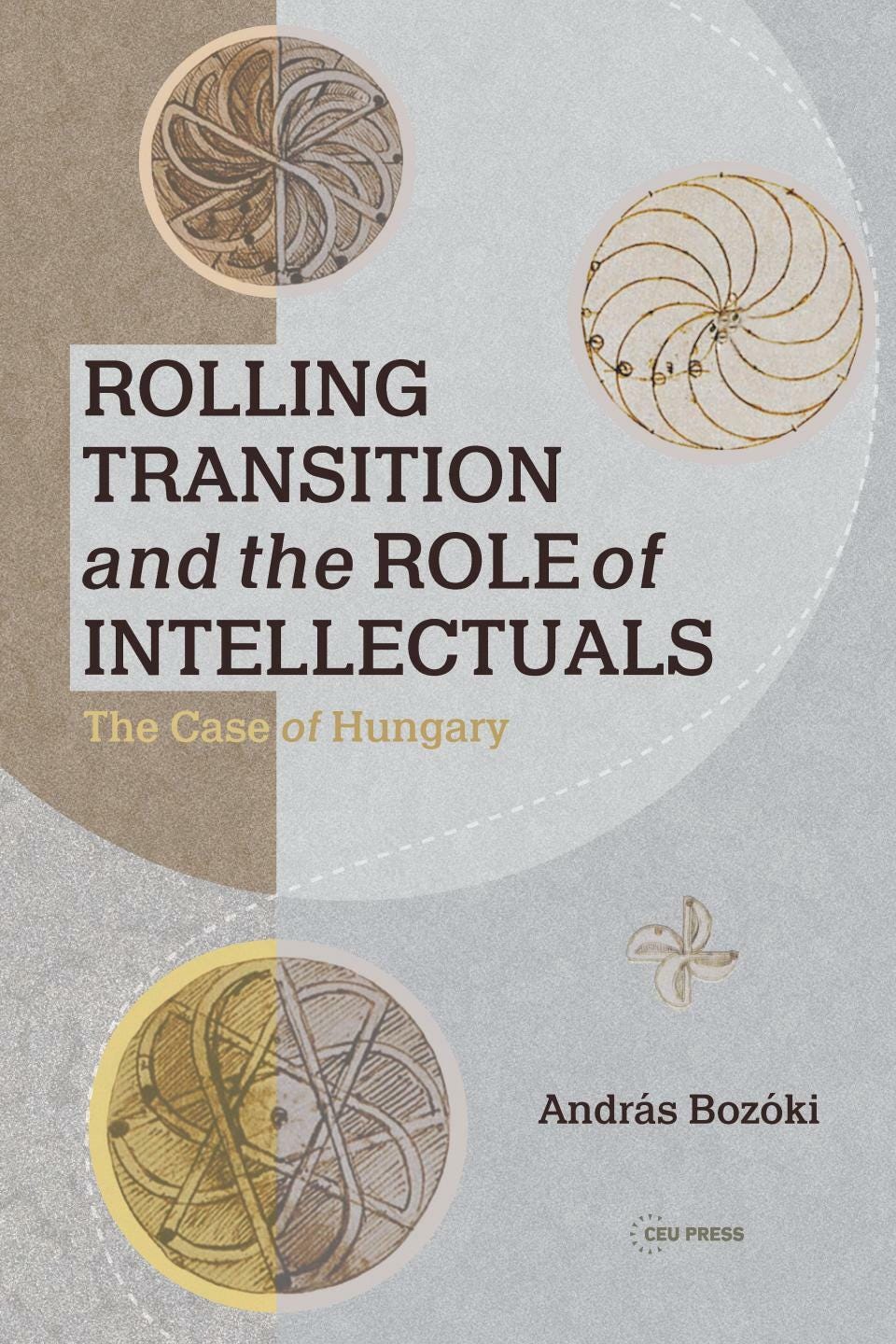本文发表于:《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1期(点击链接跳转到PDF下载页面)
友情推荐:《中国民主季刊》官方Substack账号:https://substack.com/@icdt
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旧制度与法国大革命》里讲,18世纪中叶,法国文人政治盛极一时。其典型做法是将公共政治讨论包装成“哲学”输入到文学写作中,用以引导社会舆论。其结果是文人实质上承担着主要政治家的角色,包括贵族在内,没人有能力挑战当时文人所承担的社会角色。最终这些被包装成“哲学”的新思想、新观念,成了引发法国大革命的主要诱因之一。1
关于知识分子在社会变革中承担的角色,普罗大众往往估计不足。随着反智主义情绪高涨,普罗大众反而鄙视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站在执政者角度来看,其看法却与反智主义观念截然相反,因为知识分子确实可能领导社会变革。正因如此,专制政权往往才不惜一切代价打压知识分子,包括诱导普罗大众莫名仇恨知识分子。
由知识分子领导的社会变革,较近的案例莫过于东欧剧变,尤其以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匈牙利最为突出。1977年,在捷克斯洛伐克知识分子《七七宪章》签署者团体中,作家哈维尔(Václav Havel)无疑是其中思想领袖,后来不但领导了天鹅绒革命,还当选首任捷克总统。《七七宪章》的影响力还跨越国界,引起波兰和匈牙利知识界积极响应(后来中国的《零八宪章》也受此启发)。
1976年波兰知识分子成立了“保卫工人委员会”,其骨干成员包括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和雅采克·库隆(Jacek Kuroń,后在新政府任劳工和社会政策部部长)等人,后来参与领导了著名的“团结运动”(此为推动波兰民主转型的决定性运动)。1977-1981年间,波兰知识分子团体自发复兴了该国19世纪末“飞行大学”传统,以“科学讲座协会”(Towarzystwo Kursów Naukowych)名义展开秘密结社活动(后来也汇入到“团结运动”)。其杰出成员除前面提到的两位,还包括布罗尼斯瓦夫·盖雷梅克(Bronisław Geremek,后在新政府任外交部长)、瓦迪斯瓦夫·巴托谢夫斯基(Władysław Bartoszewski,后在新政府任驻奥地利大使和外交部长)和安德烈·切林斯基(Andrzej Celiński,后在新政府任文化部长)等等,这些还不包括后来跟米奇尼克一样淡出政治的其他重要活动家。可以说波兰知识界为社会运动和社会变革贡献了巨大的才智力量,其规模和程度恐怕连匈牙利也难与之匹敌。
匈牙利也主要由知识分子推动民主转型,其形式相当与众不同。匈牙利政治社会学家博佐基·安德拉什(Bozóki András)在2022年出版的《匈牙利滚动式转型与知识分子角色》一书中,将匈牙利民主转型分为五个时期:异议时期(1977-1987)、公开网络建设时期(1988)、圆桌谈判时期(1989)、议会政治时期(1990-1991)和新民主运动时期(1991-1994)。其中该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活动,呈现打车轮战式滚动参与:如从异议时期算起,每个转型期都有大约3/4的知识分子被新加入的知识分子替换掉,剩余约1/4又进入下一转型期继续领导社会转型;主要参与者和最活跃成员像轮班或打车轮战一样,轮番参与政治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匈牙利社运知识分子自身也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成长历程:异议人士阶段、职业化阶段和建立新政权以后的新政治运动阶段。2
博佐基认为中欧国家批判型知识分子,在推动前共产政权更迭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是他们使共产主义政治体制失去了合法性,是他们形成了新的政治语言、创造了新的政治机遇,以及定义了冷战后新民主政治的全新特点。博佐基说的情况,特指“社会运动知识分子”,与已经取得一定社会地位的“体制化知识分子”相区别。二者比较关键的差别包括:体制化知识分子可能是诱发社会运动的重要力量,可以说主要负责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社运知识分子(在推动社会运动激进化进程中扮演关键角色)才是社会运动主要组织者、参与者和推动者,其主要角色是将社会问题政治化,以及推动社会来解决问题。但社会运动产生的新知识主要来自于社运知识分子,这种新知识也可能在社运知识分子和体制化知识分子之间造成紧张关系,尽管这两类知识分子也可能在社会活动中合作。3
根据博佐基的说法,米奇尼克和哈维尔显然是社运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们不但在社会运动中承担了新知识、新思想、新理论生产,还树立了新的道德权威,尤其对其他社运知识分子产生了重要影响。匈牙利知识分子群体存在较大分化,缺少跟米奇尼克和哈维尔相提并论的最突出代表,但仍然呈现出鲜明的群体性特点。1970年代以前,匈牙利就形成都市派和民粹派两大反对派团体(这一分化也延续到往后反对运动中):都市派知识分子主要由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卢卡奇(Lukács György)的学生圈子和一些作家组成,比较突出的代表有哲学家基石·亚诺什(Kis János)和作家哈拉兹第·密克罗什(Haraszti Miklós)——作家康拉德·哲尔吉(Konrád György)是社运知识分子最重要代表之一,广义上也属于这个圈子;民粹派则包括作家丘尔卡·伊斯特万(Csurka István)和诗人乔里·山多尔(Csoóri Sándor)等人。4 从这些构成可以看出,文人和思想家是匈牙利社会运动主体。
事实也确实如此。根据博佐基和西蒙·阿格尼斯(Simon Agnes)的统计,1977-1994年间,最活跃的社运知识分子占比最高的前十种职业分别是:文人(13.61%)、艺术家(13.43%)、记者(12.65%)、经济学家(7.17%)、历史学家(6.14%)、教师(6.02%)、社会学家(5.96%)、工程师(5.66%)、律师(5.54%)、大学生(4.94%)。从中可以看出,文人和人文社科类从业人员参与社会运动的热忱明显高于理工类。其中核心社运知识分子(即充当领导者角色、长期活跃以及主要影响力者)占比最高的前五种职业包括:文人(35%)、哲学家(15%)、社会学家(12.5%)、经济学家(10%)、工程师(7.5%)。依然是文人和人文社科占比最高。5
博佐基(和西蒙)并未解释这种比例构成的成因,但我们可以想象:思想最活跃和最善于表达的群体更倾向组织、参加和推动社会运动。这一点在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也可以得到验证。1976年米奇尼克重新反思波兰知识分子与天主教会矛盾来龙去脉,从中发现了知识界和天主教会可以寻求合作的契机,为将来的反对联盟跨出了关键性一步,可以说是引导波兰走向社会团结的第一步。6 哈维尔的名言“生活在真实中”则更加家喻户晓,几乎可以说树立了一种普遍的反抗信念。
但博佐基也指出,匈牙利产生社运知识分子跟该国自身环境独特性有关。1996年美国社会学家杰罗姆·卡拉贝尔(Jerome Karabel)还列举了知识分子可能反对、乃至反抗政权的八项条件,包括知识分子群体自身的组织化和政治化程度、知识分子阶层相对独立性、政权压迫性相对较低、统治集团内部分化(或自我削弱)、国家失能、历史上有反权威的文化传统等等。7 比如东德和罗马尼亚就出现了有社会运动,但知识分子缺席的奇怪现象。8
就东德的情况而言,知识分子缺席跟政权压迫性没有多大相关性(反而是一般社运人士带头克服恐惧心理)。东德政权压迫程度跟波兰比并不见得严重多少,而且两国都有教会做中间人调停政府与社会冲突(尽管有人喜欢夸大教会实际影响力,忽视教会在社会上感受到的敌意和孤立)。9 但东德知识分子为什么缺席呢?这恐怕跟该国知识分子群体自身孱弱有关系。
“社运知识分子”这个概念由耶鲁大学社会学家罗纳德·埃尔曼(Ronald Eyerman)提出,原指在社会运动中成长并起来推动社会运动发展的知识分子。10 但事实上,后来很多研究证明社运知识分子也可能先于社会运动,也就是说不一定先有社会运动才有社运知识分子。最著名的案例,莫过于在美国传播甘地思想的霍华德·瑟曼牧师(Howard Thurman)、社会活动家贝雅得·拉斯丁(Bayard Rustin)和詹姆士·劳森牧师(James Lawson),正是他们的思想传播工作引发了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后来他们也跟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一起领导这场运动)。11 可见社运知识分子形成思想传播者角色也可能先于社会运动。
博佐基的研究给中国读者带来了新的展望,也鼓励中国知识分子主动去探索新的知识生产和思想生产角色。不见得是社会运动创造这种新角色,也可能是这种新角色创造社会运动和社会变革。政治高压事实上并不能囚禁思想探索,也不能阻止社会自发寻求出路。如果有人觉得想一些前人之所未想之事也有一种遭人围追堵截的压迫感,不妨先想一想是不是自己给自己画地为牢了。
社运知识分子这一角色在中国至今缺席。一个尚未产生的新事物并不能证明其不可能产生,最多只能说明中国知识分子被想象中的“封控政策”画地为牢。如果知识分子像2022年底突破防疫封控政策那样,主动克服自身恐惧心理,主动去成为社会变革引领者,届时我们会发现,所谓政治高压也不过如此,说来说去也就是各人自己给自己画地为牢。
(完)
关注《中国民主季刊》
官方推特账号:https://x.com/chinatransition
官方网站:https://chinademocrats.org/?cat=8
Alexis de Tocqueville, The Ancien Ré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trans. Arthur Goldhamm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127-30, 15-6.
András Bozóki, Rolling Transition and the Role of Intellectuals: The Case of Hungary, 1977–1994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2022), 11, 524-6, 8. 注意:匈牙利人一般姓氏在前、名字在后(同中国和日本姓名习惯),英语出版物按英语国家习惯调整了姓名顺序;中文译名则一般尊重匈牙利习惯,将匈牙利原名“Bozóki András”译为博佐基·安德拉什,其中博佐基为姓氏。
Ibid., 60-1, 50-2.
Máté Szabó, “Hungary,” in Dissent and Opposition in Communist Eastern Europe: Origins of Civil Society and Democratic Transition, ed. Detlef Pollack and Jan Wielgohs (Ashgate, 2004), 51-71.
András Bozóki, Rolling Transition and the Role of Intellectuals, 490. 有关“文人”这种说法,原文用词是“litterateur”。在英语中,“litterateur”这种说法,对应法语的“littérateur”和“gens de lettres”,以及拉丁语的“līterātī”(单数līterātus ),跟中文的“文人”最接近。除作家之外,文化修养高的群体也可以被称为“文人”。“litterateur”这个词虽然来自拉丁语“litterātor”(指教读写和文法的教师),但其在英文读者群体中已经偏离了“litterātor”这种用法(法语也偏离了这个词的拉丁语原意),其对应的意义是“līterātus”(也即文人)。
Adam Michnik, The Church and the Left, trans. David Os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Jerome Karabel, “Toward a Theory of Intellectuals and Politics,” Theory and Society 25, no. 2 (1996): 205–33.
Helena Flam, “Dissenting Intellectuals and Plain Dissenters: The Cases of Poland and East Germany,” in Intellectuals and Politics in Central Europe, ed. András Bozóki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1999), 19-41; Irina Culic, “The Strategies of Intellectuals: Romania under Communist Rul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Intellectuals and Politics in Central Europe, ed. András Bozóki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1999), 43-71; Alina Mungiu-Pippidi, “Romanian Political lntellectuals before and after the Revolution,” in Intellectuals and Politics in Central Europe, ed. András Bozóki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1999), 73-99.
有关东德相对宽容的社会环境及其教会角色参考:Werner Volkmer, “East Germany: Dissenting Views during the Last Decade,” in Opposition in Eastern Europe, ed. Rudolf L. Tökés (Palgrave Macmillan, 1979), 113-41; Andreas Glaeser, Political Epistemics: The Secret Police, the Opposition, and the End of East German Socialism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1).
Ronald Eyerman, Between Culture and Politics: Intellectuals in Modern Society (Polity, 1994).
Sean Chabot, “Framing, Transnational Diffusion, and African- American Intellectuals in the Land of Gandhi,” in Popular Intellectuals and Social Movements: Framing Protest in Asia, Africa, and Latin Americ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19-40.